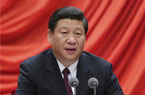近日,江蘇、上海、北京陸續推出本地高考改革技術性方案并征求意見,各地不約而同降低英語比重引起熱議。公眾將目光再一次投向了教育部,希望國家層面的高考改革方案能夠有大動作。
不過,與地方相比,中央政府部門的態度更為謹慎。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雖然沒有否認此前傳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出臺方案的時間表,但卻表示“國家層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過程中,還沒有定稿的時候,誰也不能說,因為方案隨時可能修改”。大有不到最后一刻,誰也做不了主之意。
過去的3年中,教育部已經不止一次“辟謠”,自《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之后,每一次的風吹草動都能引發人們對于國家高考改革的遐想,而只聞其聲的尷尬足見破局之難。
遲遲未決的方案
“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這是2010年《綱要》確定的高考改革思路。可以說,“頂層設計”已經初具。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具體方案卻一再推遲。
2011年初,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學習時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全面推動我國教育事業實現科學發展》的文章,就被外界看作是方案即將出臺的信號。這樣的猜測也屬合情合理:《綱要》頒布半年多之后,教育部長再次提及高考改革,自然是落實《綱要》的進一步行動。然而,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很快出面否認,稱并未公布方案。
2012年“兩會”,袁貴仁再提高考改革方案,稱正在“最后沖刺”,年內一定出臺。事實卻是,直到今年年初,《關于2013年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意見》(也稱“一號文件”)中,提出高考改革的總體目標和基本框架被提上日程。
“《綱要》出臺3年了,現在卻又繞回到了總體目標和基本框架,其實‘頂層設計’ 已經具備了,就是推行考試和招生的分離,但難點在于權力的調整和下放。”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南風窗》記者說,“政府要把辦學的自主權交給學校,把考試的評價權交給社會機構,行政部門會愿意嗎?比如國家教育考試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試院,現在由他們組織考試、擁有學生檔案的投檔權,如果變成是社會化的考試,學校自主選擇認可,學生自由選擇參加,高考就變成了以學校和學生為核心,跟教育考試部門沒有關系了,教育考試院的價值和權力就會消失。如果大學自主招生,意味著大學有辦學自主權,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教考招的分離也會推動教育行政體制的松動。”熊丙奇認為,《綱要》的方向其實已經很明確了,相關部門是否愿意放權才是問題的關鍵。
而現在,應該真正到了袁貴仁所說的 “沖刺階段”,時間表已經較為明朗,拖不過2013年,但是方案的內容卻依舊含糊,最后的定稿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綱要》的基調,決策層和相關咨詢專家的態度顯得過于謹慎。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在2013年亞洲教育論壇年會亮相時,只要提到高考,就頗為緊張:“一切都要以最后拍板的方案來,現在我不便多說。”而該中心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說,“作為紀律,方案的具體內容無法透露,只能說有所突破。”現為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考試招生咨詢工作組專家的王烽曾參與起草《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從他的態度也似乎能夠觀察到教育行政部門堅持“漸進式”方向的改革脈絡。“考試招生制度肯定是要國家層面去推動,但在實際的推動過程中,最終會落到地方,現在是16個省分省命題,每個省的情況都不一樣。這么多年地方進行了一些試驗,給招生改革提供了一些經驗和教訓。如果在全國范圍內試驗的話,影響面太大,風險也更大。”王烽說,在過去30年的改革中,地方和高校的確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然而,“地方先行”的模式卻并不被看好。針對目前地方省份推出的高考改革“新政”,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稱,各個省出臺的政策,都在一個狹窄的區域,真正核心的、體制性的東西沒有做任何的改變。而熊丙奇則認為,此次地方高考改革還是延續以前的思路,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推行高考改革,其實一直是在進行科目和分制的調整,而沒有進行錄取改革,這次地方的方案傳遞出來的信息其實都涉及這個問題。
中央主導,地方決斷?
面臨高考的屬地格局,中央很難拿出剛性的指導意見,將更多自主權交給了地方,不過在外界看來卻無異于“踢皮球”,而地方看似獲得了進行改革試驗的主導性,但由于宏觀導向的缺乏,實踐的挪騰空間極其有限。在這種困局之下,高考改革便很難突破“科目改革”的范疇。
“如果推行考試和招生的分離,顯然要進行考試的社會化,把考試招生的自主權交給大學,但地方推行高考改革的時候,還是很難打破現有的權力和利益結構。另一方面地方其實也無能為力,國家應該有一個統一方案,地方制定細則。而且全國的重點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屬的大學,也不是地方能說了算的。”按照熊丙奇的構想,高考改革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重點大學完全進行自主招生,面向全國,無論從資金來源還是屬性來講,這些院校都應該進行自主招生,各地考生可以不分戶籍自由報考,并以統一測試成績申請高校;其次,地方院校由于地方政府出資更多,可以將招生名額更多給本省的考生;此外,高職高專現在招生困難,可以不必要求考生參加高考,而實行申請入學,至于學校的辦學管理,則實行寬進嚴出。
盡管熊丙奇自認從這三個層面改革,所有的問題都會引刃而解,不過他也感到從目前教育部的“漸進式”改革思路來看,顯然過于“理想化”。他說,參照異地高考改革的路徑,對未來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也不必過于期待。
去年,曠日持久的異地高考權利之爭終于有了“結果”。到目前為止,全國31個省市除西藏外均出臺了異地高考方案。從中央政府的政策意見可以看出,異地高考采用的是“中央指導,地方決斷”的模式,這也是其政策效能被詬病的原因,按照這一模式,矛盾最為集中的北上廣都采用了設置 “門檻”的階梯式方案,北京只允許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北京報考高職院校。上海的隨遷子女異地高考則采取與居住證掛鉤的積分制。在本次高考制度改革“頂層設計”當中仍然不會有實質性進展。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續梅近日即公開表示,隨遷子女的異地高考問題,這次還是按照去年底國務院發布的文件精神。
以中央為主體的政策通過“頂層設計”、“頂層推動”等策略解決社會問題,而以地方為主體的政策則以先行先試、因地制宜為特征。實質上是一種放權分責的策略,賦予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權力,以規避中央政府頂層設計帶來的風險。按照教育部官員的說法,異地高考“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要考慮城市承載能力,尤其要考慮影響原戶籍居民的考生利益”。
盡管中央教育改革的規格越來越高,但它所承擔的責任卻并未與之匹配。早在2010年,國務院成立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的劉延東親自擔任組長。此后,為完善改革決策咨詢機制,2010年11月,國家層面又成立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這是中國教育史上首次設置專門機構對國家教育重大改革發展政策進行調研、論證和評估。2012年7月,為對國家教育考試制度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成立,由教育、科技、經濟、法律、管理等領域的26名專家組成。
然而,適時靈活的策略性調整造成了權責配置失衡的缺陷。作為一項全國性的改革,高考改革存在事權分配關系,但這種分配不是建立在制度規定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靈活度大但權威性相對低的政策規定上。同時,由于權力和其他資源的分配往往是通過上下級政府的討價還價來確定,責任的認定也不得不依據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所以極易導致主體虛置的現象。
放權能否實現
回顧30年的高考制度變遷,從“文革”結束后,初步確立了“全國統考、地方審核、學校錄取”的高考模式,到上世紀80年代“國家計劃招生、用人單位委托招生和招收少數自費生”三種辦法的執行再到之后的分省命題,雖然招考形式不斷改革,但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單位組織招生的超穩定結構一直存在,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以省為單位的分數線劃定標準以及招生分配指標制度等一系列規則共同構成了地方利益。
“很顯然,所有問題都出在集中錄取制度上。地方割據本身是由于招生制度的計劃分配方式,名額分到了不同的地方,自然就變成了地方的利益。”熊丙奇說,如果不改變錄取的計劃體制,所有的努力很可能淪為“偽改革”。
多位學者認為,在現有的框架下,自主招生、向大學放權有可能會是最大的突破口。王烽也表示,自主招生應該會有進一步的激勵措施。
自主招生從2003年開始推行至今,參加自主招生的院校擴展到80多所,并逐漸形成了“北約聯盟”11校,“華約聯盟”7校、“卓越聯盟”9校,“北京高科聯盟”11校聯考的模式。而實際上,高校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招生選拔權,但仍受制于高考分數線這一“緊箍咒”。“戴著鐐銬跳舞”的招生體制改革并未真正觸及自主招生的本質,變成了高校“掐尖”,已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對此,王烽認為,如果說 “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是從技術操作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那么“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則是體制上的設計,調整的是各個主體的權力和責任。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擴大,要求建立保證招生公平的新機制,首先是對高校的約束和監督、問責機制。學校主導的多元評價標準的建立,意味著高校招生工作中綜合評價重心的轉移,即由以考代招體制下的考試機構和政府招生辦公室為主,轉變為以高校為主。“不過,多數高校對落實招生自主權還沒有做好準備,也并不是很積極,都不愿意碰這個事,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主招生的重要性。”王烽說。
高校的態度其實也不難理解,自主雖然意味著權力的增加和回歸教育本質的可能性,但是在其本身的行政化之下,也意味著政策風險和輿論風險,高校自身如何破除招生“潛規則”、陽光運行,也是改革的對象之一。作為權力的被讓渡者,尚且沒有做好準備,需要交出招生規則和程序等權力的政府部門又做好準備了嗎?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